乡村振兴中的投融资支持与机制创新
乡村振兴中的投融资支持与机制创新
乡村振兴还离不开农业概念。农业总体而言的发生领域就是农村,进一步形成了“三农”概念。我们一向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人类社会的供给体系中,具有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但是在各个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观察到: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展,农业作为产业,又面临相对弱势的问题和一系列的矛盾。我国领导层在前些年就强调了农业需要得到反哺,内在逻辑就是农业的比较利益是相对低下的,它在产业中间是居于弱势地位的。“三农”问题的合理解决,需要得到必要的统筹规划和政策支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农村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而在继续发展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和农业、农村、农民(“三农”)有关的一系列的挑战。
总的来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间,城乡一体化、农业产业化、新型城镇化,所内含的人本立场上的诉求是要使农民致富。当然农民在总人口中间的比重是呈下降趋势,但始终还是存在着务农的社会成员,这些成员要融入全面小康与共同富裕;而且,未来几十年间的城镇化推进中,不应使几亿农民有序地实现市民化——从现在来看,粗线条地讲,未来几十年,中国至少还有3-4亿人口要从农村转为城市常住人口,并应尽可能顺利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市民”待遇。而留在农村区域的这些成员,他们所关联的产业要纳入总体的全局的可持续发展中,同样也需要实现升级。这种一体化发展中产业的升级和乡村的振兴,其实是一个事情在两个角度上的表述。
乡村的振兴,不排除非农产业在其中的结合和渗透,但毕竟乡村概念下,基本面上首先还是农业要有现代化,农业要有升级发展。当然,中央的指导方针非常清晰:我们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上,才能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支持高质量升级发展。这样,在农村发展的大视角来看,不同的区域,农业方面相关的不同市场主体、企业,都需要得到投融资的有力支持,还要紧密结合着这种支持的政策设计,要考虑相关的机制创新。
很多情况下,光讲政策其实问题说不全,必须考虑相关的制度机制怎样在现代化转轨的过程中有创新的积极努力,再配上政策的优化支持。在结合中国基本情况的制度创新、政策优化、支持乡村振兴这方面至少有三个着眼点必须加以强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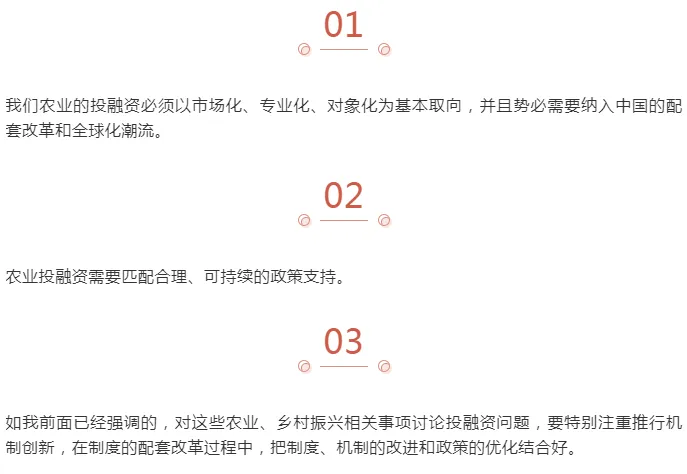
从市场化视角来说,政府的农业投融资要回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尊重市场资源配置的机制起总体而言的决定性作用。农业里有企业介入进来后的规模化经营、集约化经营的投融资,要充分运用市场主体的自主权,在竞争和合作中间争取做好、做大、做强。
在所谓专业化的视角上,要强调各项农业的投融资要以高标准的专业水平为取向,注重提高绩效。
所谓对象化是说,各项农业投融资要有效地针对投资项目的特点,切合种植或者养殖的客观情况,形成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的供给管理解决方案。可行性的研究、金融工程式的一些定制,都要抓好优化落实适应特定对象的供给,这正是对应中央所说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体系质量效率提高”的理念。在现实生活中,一定是要求有定制化的解决方案,而且要求这种方案尽可能地高水平——它是要处理每一个具体项目上带有挑战性的一些结构性问题。
以此为背景,我们要推进配套改革的整体化:比如说和农村的产权制度等改革的呼应和协调。大家都越来越感受到,农村改革推进了这么几十年,在进一步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方面,这个问题的挑战其实是相当严峻的。必须和农村的社会治理变革相结合着把它处理好。
在“有中国特色”之下的难题,我简单地说几句。我观察,一向表述的我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被称为“集体所有制”,也被认为是公有制,但它和其他的建成区(凡是城镇区域、工矿区域)的那个土地所有制不一样——后者被称为国有制。
可以比较直率地说,在实际生活中,随着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机制要升级,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提高完善程度,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为底盘的农村区域要素合理流动之路,是越走越窄了:因为在经济性原理上分析,集体所有制的决策机制是什么?是集体成员为一个圈子,在整个社会里面是个小圈子,一人一票。从人性来说,一人一票的决策机制导致的最近似的结果,是这个圈子所掌握的那个所谓集体所有的土地,一人一份,但是这个圈子的边界是在不断变化的——比如村里的姑娘嫁出去了,她不是这个集体的人了,这时候怎么变动这套原则、机制下对她的土地分配呢?外面的姑娘嫁到村里来,是村里的媳妇了,成为村集体成员了,她怎么取得与这样一份土地实际对应的权属呢?实际生活中间,这些事情关联的各种矛盾纠缠在了一起。还不要说其他人员变动、生老病死各种各样的情况,集体成员的边界必然模糊和不断变化。所谓集体决策、一人一票,在实际生活中——调研就可以知道——越来越变成一个更小群体的、这个圈子里面有主导权者的决策,而这个决策如果出偏差怎么纠正?和外部的生产要素流动怎么对接?越来越成为难题。
另外还有,我们强调的“全球化”,这里面应既有经验的交流、分享,也有各国政产学研商各界相关的合作和互动中的正面效应。中国现在是义无反顾地拥抱全球化,要化解逆全球化的逆流对我们造成的不利影响;中国广大农村区域,也一定是在这个潮流中对应全球化的供需循环与多因素交流的。在农业和相关事项投融资方面,政策支持伴随着机制创新。在问题导向之下,应该积极考虑的有多个方面。
比如,加强各个部门涉农资金的优化整合、组合、协调运用。这就是要依照中央现在所重视的系统论思维,一定要通过大部扁平化改革取向之下、结合着各个部门协调机制优化的种种努力,来把这个事情做好。
财政主导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和产业基金的乘数放大效应,要充分发挥。它的实现要对接的,我认为一定是政策性金融的概念。财政用的公共资源是政策性资金,要区别对待,以体现政策,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即要体现内在的特定的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属性。政策性资金要对接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杠杆式放大——这就又跟商业性信贷金融对接了。
还有,对农业领域里的企业投资要合理激励。其实很多企业觉得自己有相对优势,可以在乡村振兴、农村开发中一显身手;这也必然和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对接——股市、债市、知识产权市场都要对接到这样一个有制度规则公平正义、培养长期行为的市场上去。
还有循环经济模式的创新——涉及我们所说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的开拓。这里所说的循环经济,早就看到有一些经验的总结。像广西的恭城(桂林附近),百姓过去形成一定的养猪习惯,而且政府又鼓励更多农户养猪:猪粪可以入沼气池,沼气池可以产生沼气能源,可以替代原来破坏植被的砍树烧柴行为,提高百姓在农村的生活质量;而且每隔一段时间,清理出的沼气池里的沼渣、沼液,又是很好的有机肥,这些肥施到果园里,又有高品质的果品产出,这些果品产出又可以对接到有“客户体验”的农家乐采摘、旅游……这个链条上是循环经济的特色,但到了一定规模化运营的时候,需要有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合作,来做一些特定的连片开发性质的项目建设。
与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并行不悖的乡村振兴,城乡接合部的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结合,总体来说,政府方面一定要掌握好“规划先行、多规合一”基础之上的政策配套、细化优化。国土开发实施后一旦发现通盘规划犯错误,如要再改正,成本是极高的,甚至有的时候是难以再把它改回来的。
总体的中国和外部世界对接的“命运共同体”式发展中,面对“三农”的国际合作和新技术革命,也非常有前景。“一带一路”上的生态农业园区、农产品与相关产品的加工基地、物流中心、“冷链”及相关的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创新升级的市场营销等,这些事情我们都要在现实生活中积极探讨它们的进步和发展。
 领导关怀
领导关怀